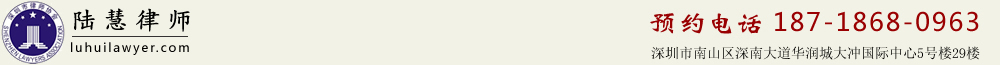首頁 > 刑事辯護
刑事辯護
不當(dāng)討債行為不可能成立尋釁滋事罪
發(fā)布時間:2020-12-17 11:04:54 瀏覽次數(shù):
不當(dāng)討債行為不可能成立尋釁滋事罪
文 | 張明楷 清華大學(xué)
文 | 張明楷 清華大學(xué)
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數(shù)維權(quán)行為是完全合法的,只是部分維權(quán)行為可能存在瑕疵或不當(dāng)之處,極少數(shù)維權(quán)行為也可能因為違反法定條件而構(gòu)成違法犯罪。
本文所要表達的核心意思是,既然行為人實施的是維權(quán)行為,就表明相對方存在違法乃至犯罪行為; 因此,維權(quán)人的利益優(yōu)越于相對方的利益; 不能僅因維權(quán)行為存在瑕疵或者不當(dāng),就直接將其作為犯罪處理,更不能將完全合法的維權(quán)行為當(dāng)作犯罪處理,否則就不可避免侵害合法權(quán)益、助長違法犯罪。
更為重要的是,刑罰的目的是減少、預(yù)防犯罪,而不是為了懲罰而懲罰,更不能為了完成某種指標(biāo)而懲罰行為人。
如果不是以刑罰目的為指導(dǎo)辦理刑事案件,刑事司法就喪失了正當(dāng)性、合法性; 應(yīng)當(dāng)杜絕完全不顧及懲罰活動是否助長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的刑事司法活動。
要避免刑事司法助長違法犯罪,就必須妥善處理各種維權(quán)行為,防止“惡人先告狀”。下面就當(dāng)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幾類情形作簡要說明。
債權(quán)人具有使債務(wù)人清償債務(wù)的權(quán)利,但如果為了討債而非法拘禁、傷害、殺害債務(wù)人的,無疑成立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
但是,當(dāng)前的司法實踐大量地將債權(quán)人對債務(wù)人采取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方式實施的討債行為,認定為尋釁滋事罪。在本文看來,這種做法明顯不當(dāng),應(yīng)當(dāng)杜絕。
既然相對方存在債務(wù),債權(quán)人就有討債的權(quán)利; 在債務(wù)人不履行債務(wù)的情況下,債權(quán)人采取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方式討債,是為了實現(xiàn)正當(dāng)目的。
如果索要的利息在司法解釋規(guī)定的限度之內(nèi),完全是正當(dāng)?shù)? 如果利息超過了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債權(quán)人就沒有超過的部分索要利息,也是正當(dāng)?shù)摹?br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13年7月15 日《關(guān)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以下簡稱《解釋》)第1 條第1、2、3 款分別規(guī)定: “行為人為尋求刺激、發(fā)泄情緒、逞強耍橫等,無事生非,實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guī)定的行為的,應(yīng)當(dāng)認定為‘尋釁滋事’。”
“行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發(fā)矛盾糾紛,借故生非,實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guī)定的行為的,應(yīng)當(dāng)認定為‘尋釁滋事’,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發(fā)或者被害人對矛盾激化負有主要責(zé)任的除外。”
“行為人因婚戀、家庭、鄰里、債務(wù)等糾紛,實施毆打、辱罵、恐嚇?biāo)嘶蛘邠p毀、占用他人財物等行為的,一般不認定為‘尋釁滋事’,但經(jīng)有關(guān)部門批評制止或者處理處罰后,繼續(xù)實施前列行為,破壞社會秩序的除外。”
據(jù)此,不當(dāng)討債行為不可能成立尋釁滋事罪。
(1) 債權(quán)人向債務(wù)人討債,不管是不是高利貸,都不可能屬于為尋求刺激、發(fā)泄情緒、逞強耍橫等,無事生非實施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行為。
(2) 債權(quán)人向債務(wù)人討債的行為不可能屬于借故生非。況且,債權(quán)人之所以實施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行為,就是因為債務(wù)人不履行債務(wù),亦即,完全屬于“被害人故意引發(fā)或者被害人對矛盾激化負有主要責(zé)任”。
(3) 既然行為人因債務(wù)糾紛,實施毆打、辱罵、恐嚇?biāo)嘶蛘邠p毀、占用他人財物等行為的,一般不認定為尋釁滋事,那么,債權(quán)人對債務(wù)人實施的類似行為,就更不能認定為尋釁滋事。
(4) 即使債權(quán)人反復(fù)向債務(wù)人實施相關(guān)行為,或者經(jīng)有關(guān)部門批評制止或者處理處罰后,繼續(xù)實施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行為,也不可能成立尋釁滋事罪。正是因為債務(wù)人不履行債務(wù),債權(quán)人才反復(fù)追討,如果債務(wù)人一經(jīng)追討就履行了債務(wù),債權(quán)人則不會繼續(xù)追討。
將債權(quán)人對債務(wù)人采取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方式實施的討債行為以尋釁滋事罪論處,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認定犯罪的前提是行為符合相關(guān)犯罪的構(gòu)成要件,但對構(gòu)成要件的理解與適用要以保護法益為指導(dǎo)。
抽象地說,尋釁滋事罪的保護法益是“公共秩序”,“公共秩序”是一種社會法益。但是,“社會法益只是個人法益的集合,是以個人法益為其標(biāo)準(zhǔn)所推論出來的。個人的一切法益都是得到法律的承認和受法律保護的,而社會法益的保護是受到限制的。……
因此,只有當(dāng)某種社會利益與個人法益具有同質(zhì)的關(guān)系、能夠分解成為個人法益( 即系個人法益的多數(shù)之集合) 、是促進人類發(fā)展的條件且具有重要價值和保護必要時,才能成為刑法所保護的社會法益”。
換言之,保護社會法益的目的也是為了保護人的法益,所以,必須聯(lián)系個人法益確定尋釁滋事罪的保護法益。
質(zhì)言之,由于尋釁滋事罪存在四種類型,需要具體考察各種類型的具體法益。禁止“隨意毆打他人”的規(guī)定所欲保護的法益,應(yīng)是與公共秩序相關(guān)聯(lián)的個人的身體安全。否則,難以說明尋釁滋事罪在刑法分則中的順序與地位。
正因為如此,行為人隨意毆打家庭成員的,或者基于特殊原因毆打特定個人的,沒有侵犯該法益,不可能成立尋釁滋事罪。
禁止“追逐、攔截、辱罵他人”的規(guī)定所欲保護的法益,應(yīng)是一般人在公共生活、公共活動的行動自由與名譽,也可以說是與公共秩序相關(guān)聯(lián)的行動自由與名譽。
所以,在沒有多數(shù)人在場的情況下,辱罵特定個人的,不屬于尋釁滋事罪中的辱罵他人。禁止“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的規(guī)定所欲保護的法益,是與財產(chǎn)有關(guān)的社會生活的安寧或平穩(wěn)。
因此,行為人侵入他人住宅損毀他人財物的,或者已婚子女強拿硬要父母財物的,不成立尋釁滋事罪。禁止“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的規(guī)定所欲保護的法益,顯然是不特定人或者多數(shù)人在公共場所從事自由活動的安全與順利。
不當(dāng)討債的真實案件,都是在特定的時間、地點針對特定的債務(wù)人實施的行為,都不是發(fā)生在公共場所,根本不可能擾亂公共秩序和破壞社會秩序,完全不具備尋釁滋事罪的本質(zhì)。
反復(fù)特定的債務(wù)人追債的,不管有多少債務(wù)人,也不可能破壞社會秩序。將《刑法》第293 條中的“毆打”“辱罵” “恐嚇” “強拿硬要”等字面含義作為大前提,而不考慮其背后所欲保護的法益,就必然不當(dāng)擴大處罰范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不可否認,對法條文字可能作出多種不同的解釋,在刑法條文沒有修改情況下,通過司法解釋進行犯罪化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刑法分則對大量犯罪規(guī)定了“情節(jié)嚴(yán)重”“數(shù)額較大”等量的限制條件。
與以往相比,刑事司法放寬對情節(jié)嚴(yán)重的認定標(biāo)準(zhǔn)、降低數(shù)額較大的起點標(biāo)準(zhǔn),就意味著犯罪化。
再如,有些行為實質(zhì)上具有嚴(yán)重的法益侵害性,原本屬于刑法明文規(guī)定的犯罪行為,但由于某種原因,刑事司法上未能以犯罪論處。后來刑事司法改變態(tài)度,對該行為以犯罪論處,從而實行犯罪化。
但是,司法上的犯罪化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的條件: 一是行為的法益侵害程度必須達到了值得科處刑罰的程度; 二是必須遵守罪刑法定原則,不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予以犯罪化。
誠然,一個解釋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是難以判斷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刑法分則對A行為規(guī)定了較輕的法定刑,而司法解釋或者司法機關(guān)卻將比A 行為更輕微的B 行為規(guī)定為或者認定為較重犯罪,基本上就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
將債權(quán)人對債務(wù)人采取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方式實施的討債行為以尋釁滋事罪論處,違反了刑法的公平正義性。
《刑法》第238 條第1 款規(guī)定: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quán)利。具有毆打、侮辱情節(jié)的,從重處罰。”
第3款規(guī)定: “為索取債務(wù)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兩款的規(guī)定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7 月13 日《關(guān)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wù)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規(guī)定: “行為人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wù),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
既然對于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wù)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行為,也只能認定為非法拘禁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quán)利”,那么,如果將債權(quán)人為索取債務(wù)而實施的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行為認定為尋釁滋事罪,適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法定刑,乃至對多人多次實施的上述行為適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處罰金”的法定刑,就必然違反了刑法的公平正義性。
概言之,根據(jù)舉重以明輕的當(dāng)然解釋原理,對于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wù)而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行為,就不能以尋釁滋事罪論處,否則,就違反了刑法的公平正義性與《刑法》第5 條規(guī)定的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
將債權(quán)人對債務(wù)人采取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方式實施的討債行為認定為尋釁滋事罪,不符合法秩序統(tǒng)一性的原理。眾所周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切實解決執(zhí)行難”“依法保障勝訴當(dāng)事人及時實現(xiàn)權(quán)益”。
為貫徹落實上述部署,最高人民法院2016 年3 月在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提出“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zhí)行難問題。”
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2019 年7 月14 日《關(guān)于加強綜合治理從源頭切實解決執(zhí)行難問題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 指出: “人民法院執(zhí)行工作是依靠國家強制力確保法律全面正確實施的重要手段,是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quán)益、實現(xiàn)社會公平正義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
做好執(zhí)行工作、切實解決長期存在的執(zhí)行難問題,事關(guān)全面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施,事關(guān)社會公平正義實現(xiàn),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xí)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全局和戰(zhàn)略的高度,將解決執(zhí)行難確定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內(nèi)容,作出重大決策部署。
三年來,在以習(xí)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lǐng)導(dǎo)下,在各地各有關(guān)部門共同努力下,執(zhí)行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
同時,一些制約執(zhí)行工作長遠發(fā)展的綜合性、源頭性問題依然存在,實現(xiàn)切實解決執(zhí)行難的目標(biāo)仍需加倍努力。”我國的民事司法近些年來一直在對“老賴”采取各種懲罰措施,推進社會誠信體系建設(shè),以保護債權(quán)人的合法權(quán)利。
如果刑事司法將不當(dāng)討債行為認定為尋釁滋事罪,就必然助長“老賴”的形成和囂張。可是,現(xiàn)在形成了民事司法打擊“老賴”,刑事司法保護“老賴”的局面,這顯然損害了法秩序的統(tǒng)一性,值得各級司法機關(guān)深刻反思。
例如,《意見》強調(diào)“完善失信被執(zhí)行人聯(lián)合懲戒機制。各有關(guān)部門盡快完成與國家‘互聯(lián)網(wǎng)+監(jiān)管’系統(tǒng)及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聯(lián)合懲戒系統(tǒng)的聯(lián)通對接和信息共享,做好失信被執(zhí)行人身份證、護照等所有法定有效證件全部關(guān)聯(lián)捆綁制度,將人民法院發(fā)布的失信被執(zhí)行人名單信息嵌入本單位‘互聯(lián)網(wǎng)+ 監(jiān)管’系統(tǒng)以及管理、審批工作系統(tǒng)中,實現(xiàn)對失信被執(zhí)行人名單信息的自動比對、自動監(jiān)督,自動采取攔截、懲戒措施,推動完善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信用監(jiān)督、警示和懲戒體系。
建立執(zhí)行聯(lián)動工作考核機制,對失信被執(zhí)行人信用監(jiān)督、警示和懲戒機制落實情況開展專項檢查,加大考核和問責(zé)力度。規(guī)范失信名單的使用,完善糾錯、救濟機制,依法保護失信被執(zhí)行人的合法權(quán)益。”
可是,如果在民事執(zhí)行方面完善對失信被執(zhí)行人的懲戒機制,但在刑事領(lǐng)域卻對討債行為以犯罪論處,不僅導(dǎo)致二者的沖突,而且導(dǎo)致民事領(lǐng)域的執(zhí)行失效。
事實上,不少“老賴”就是在拒不執(zhí)行或者不能執(zhí)行民事判決的情況下,告發(fā)債權(quán)人構(gòu)成尋釁滋事罪乃至屬于黑惡勢力的,公安、司法機關(guān)對債權(quán)人的立案、偵查與審判,不僅使“老賴”逃避了債務(wù),而且使刑法與刑事司法成為“老賴”惡意利用的工具。
再如,《意見》指出: “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shè)。建立覆蓋全社會的信用交易、出資置產(chǎn)、繳費納稅、違法犯罪等方面信息的信用體系,完善失信聯(lián)合懲戒機制,建立完善公共信用綜合評價與披露制度,暢通市場主體獲取信息渠道,引導(dǎo)市場主體防范交易風(fēng)險,從源頭上減少矛盾糾紛發(fā)生。”
我們顯然難以認為,不執(zhí)行人民法院的判決才是失信人員,而不向債權(quán)人清償債務(wù)的人就不是失信人員。事實上,只要將債權(quán)人的行為認定為犯罪,債務(wù)人基本就逃避了債務(wù)。
所以,如果將債權(quán)人實施的跟蹤、糾纏、恐嚇、辱罵等行為以尋釁滋事罪論處,不僅必然鼓勵債務(wù)人逃避債務(wù),而且會鼓勵一些人實施借款詐騙行為。
這種不符合刑罰目的的做法,會使刑事司法喪失合理性、合法性。所以,公安、司法機關(guān)不僅不能將上述討債行為認定為犯罪,而且要特別警惕“老賴先告狀”。如果支持“老賴先告狀”,就必然侵害合法權(quán)益、助長違法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