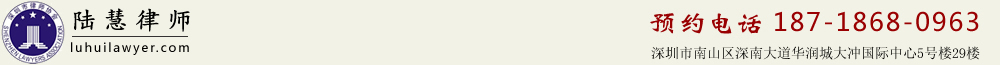刑事辯護
假冒毒品交易成功應認定販賣毒品未遂
假冒毒品交易成功應認定販賣毒品未遂
【案情】
群眾張某舉報被告人徐某販賣毒品,民警即安排其與被告人徐某聯系購買毒品。當日14時許,被告人徐某與舉報人來到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百富賓館旁旭升單車行門口,徐某以人民幣500元的價格將一小包白色粉末當作毒品海洛因(俗稱“白粉”)販賣給舉報人。交易完成后,伏擊民警當場將被告人徐某抓獲,并繳獲疑似海洛因白色粉末一小包。經鑒定,該疑似毒品白色粉末重5.97克,未檢出常見毒品成分。
被告人徐某一審當庭認罪,辯解稱其屬于犯罪未遂,是初犯偶犯,認罪態度好,請求從輕處罰。二審時徐某上訴提出:本案存在犯意引誘的情況,一審在量刑時未予考慮,明顯量刑過重。
【分歧】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產生三種爭議,分別是:一、被告人徐某出售的“白粉”未檢出常見毒品成分,即其販賣了假冒的毒品,該行為應當如何定性?是認定詐騙罪還是販賣毒品罪?二、被告人徐某販賣假冒毒品并交易成功,是認定犯罪既遂還是犯罪未遂?三、偵查機關采取特情貼靠、接洽而破獲的案件,是否屬于犯罪引誘?
筆者將對三個問題的正反兩種意見分別予以評析。
【評析】
一、販賣假冒的毒品,應認定為販賣毒品罪
詐騙罪必須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是直接故意,客觀上是用欺騙的方法去騙取財物。具體到本案,如果要認定詐騙,就是要求被告人徐某主觀上明知其獲取的“白粉”是假冒的毒品,客觀上仍欺騙買家,騙取買家財物。而詳細調查徐某對涉案“白粉”的認知,可知其一直認為自己從老鄉手里獲取的是毒品而予以出售,并無欺騙的主觀故意與客觀行為,故本案不能將徐某出售假冒毒品的行為認定為詐騙,只能從其主觀故意出發,認定為販賣毒品。
二、販賣假冒毒品即使交易成功,也應認定為犯罪未遂
交易成功,看似是故意犯罪的完成形態,理應認定為犯罪既遂。但是上文已分析本案被告人的主觀心態與定性,如果其本來就想出售假冒毒品并交易完成,自當認定為犯罪既遂,此時的既遂實為詐騙行為的既遂;而本案被告人并無詐騙的故意,其本意是想出售真的毒品卻無意間完成了假冒毒品的交易,此時不能認定為販賣毒品的既遂。
筆者認為,關于既遂的認定,法理上的“目的說”提出:所謂犯罪既遂,是指行為人故意實施犯罪行為并達到了其犯罪目的情況。主張既遂與未遂的區別就在于行為人是否達到了其犯罪目的,達到犯罪目的的是犯罪既遂,未達到犯罪目的的是犯罪未遂。從這個角度可以很好地分析本案被告人的行為特征,徐某的目的是出售真的毒品“白粉”,而其將假的“白粉”交付給買家并已交易成功,卻并未達到其販賣毒品的目的,故其交易成功也只能認定為販賣毒品的未遂。
筆者的上述兩方面分析,早已得到司法解釋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規定:“明知是假毒品而冒充毒品販賣的,以詐騙罪定罪處罰。不知道是假毒品而當作毒品走私、販賣、運輸、窩藏的,應當以走私、販賣、運輸、窩藏毒品犯罪(未遂)定罪處罰。”該司法解釋言簡意賅,但對相關問題的爭議已起到定分止爭的作用,筆者的上述分析,無非是試圖深入理解與論述該解釋。
三、偵查機關采取特情貼靠、接洽而破獲的案件,并非犯罪引誘
毒品犯罪往往具有高度隱蔽性的特點,毒品交易極少在公開場合展現給公眾觀看,更不會給司法機關提供掌握證據的時間與空間。因此,在司法實踐中,運用特情偵破毒品案件,確實是打擊毒品犯罪的行之有效的手段。雖然特情介入的程度存在不同的情形,但是“大連會議紀要”明確規定:“對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證據證明已準備實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貼靠、接洽而破獲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誘,應當依法處理。”
本案被告人徐某在案發前即已持有涉案的“白粉”,其老鄉轉送“白粉”時說“這小包白粉可以賣500元人民幣”,徐某“于是就收下了這包毒品白粉并藏在我經營的補鞋店”。買家問徐某有沒有毒品,其“想起補鞋店里面還有這包毒品‘白粉’,于是就打電話說我手上有五百塊錢的毒品要出手賣掉,問他需不需要。”可見,徐某系典型的持毒待售,所以偵查機關采取特情接洽的行為,不存在犯罪引誘。
(作者:武文芳 李磊 作者單位: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