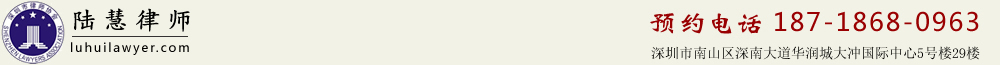刑事辯護
毒品代購者“蹭吸”行為之性質
案情
吸毒人員甲與吸毒人員乙平日相互認識。甲知道乙有購買毒品的渠道。2020年1月10日,甲給乙打電話,要求乙幫助其購買冰毒10克用于吸食。乙考慮到手頭拮據,且與甲相識已久,不好意思直接賺取差價,便提出要“蹭吸”毒品五次。甲同意乙的條件后,按照行價轉賬3.5萬元給乙。乙隨后找到經常販賣毒品的丙,聯系購買事宜。丙則提出10克冰毒最少需要付3.5萬元,乙就將甲給的3.5萬元全部轉付給丙,并與丙確定了交貨地點。而后,乙騎共享單車來到與丙約定的市區內某小區北門小樹林附近,取得10克冰毒后,全部交與甲。甲乙兩人共同吸食兩次后被抓獲,剩余毒品被查獲。
分歧
本案中,吸毒人員甲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丙構成販賣毒品罪均無疑義,但對于乙代甲購買冰毒行為的性質認定產生了分歧。一種觀點認為,以牟利為目的的毒品代購行為中的“利”包括冰毒等物質性利益,乙提出“蹭吸”要求后,在客觀上又實施代購行為,促成了10克冰毒交易的成立,故乙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第二種觀點認為,代購的冰毒是求購者用于自己吸食的,在無證據證明代購毒品者具有牟利目的時,應該認定其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第三種觀點認為,乙為了“蹭吸”而幫助他人購買毒品,目的是自己能吸食冰毒,因為沒有販賣行為,不構成犯罪。
評析
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通過專項調研發現,在很多毒品案件中,都存在有的被告人幫助吸毒人員代為購買毒品,但是沒有直接獲得金錢利益,只是與吸毒人員一起吸食所購買的毒品,即“蹭吸”的情況。這種情況是否認定具有“牟利”的目的行為,直接關系到被告人是否認定為犯罪以及此罪與彼罪。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出臺的《大連會議紀要》中明確規定,毒品代購人員為他人代購用于吸食的毒品,趁機從中牟利的,應當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2014年出臺的《武漢會議紀要》進一步明確,行為人為他人代購僅用于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開銷之外收取“介紹費”“勞務費”,或者以販賣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為酬勞的,應視為從中牟利,屬于變相加價販賣毒品,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在審判實踐中發現,“蹭吸”存在多種情況,《大連會議紀要》和《武漢會議紀要》沒有明確涵蓋 “蹭吸”行為的所有性質,加之法律亦沒有明確的相關規定,導致對于這類代購毒品行為的定性存在很多爭議。筆者認為,對于被告人代購毒品并“蹭吸”是否存在牟利之目的的認定,必須先厘清“利”的準確內涵,并結合“蹭吸”毒品的數量和次數以及所付出必要勞動的價值等情況綜合認定,不能一概而論。
“利”的一般通常理解是“收獲”的意思。牟利主要是指謀取利益,有所收獲。在此理解,應該為被告人通過自己代購冰毒的行為所得到的帶有利益價值的金錢或財物,但是不應該包括被告人為此而支付的財物或者是被告人的直接必要的勞動報酬。那么,作為刑法規定的“非法物”毒品——冰毒而言,屬不屬于“利”?一般而言,“利”應該做廣義的理解,即滿足作為主體人的物質或者精神需求的物品,既包括合法產品,也包括非法產品,對人或者一類人具有一定的價值即可。因此,毒品也屬于“利”的范疇。對此,從《武漢會議紀要》中所作的規定“或者以販賣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為酬勞的,應視為從中牟利”內容也可以得以印證。既然毒品屬于“利”的范疇,是否所有“蹭吸”行為都屬于牟利行為?對此,筆者認為,應該運用勞動價值衡量的方式來確定。具體而言,綜合全案考慮比較毒品代購者代購行為所付出勞動的價值及必要支出價值與“蹭吸”毒品數量的價值,如果后者價值明顯超出前者價值,則“蹭吸”就是非法獲利的一種表現形式,則應視為從中牟利。
就本案而言,乙缺少資金不能滿足自己吸食毒品的需求,在甲找到乙要求代購毒品時,又因為二人非常熟悉,而不好意思直接賺取代為購買毒品的差價,卻又不甘心放棄代購毒品獲得利益的機會,進而提出“蹭吸”毒品五次的要求。這表明,乙在甲找他代購毒品時,就以“蹭吸”作為他代購毒品的主要目的,而且要多次“蹭吸”。而乙在代為購買毒品的過程中,只是接打電話各一次,騎共享單車取毒品交給甲。本案中,“蹭吸”五次毒品的價值已經遠遠超過乙代購毒品過程中的必要勞動價值和全部支出,總體上不屬于代購毒品者應該得到的專門補償其毒品代購過程中所損失的利益和必要的勞動報酬,是必要損失補償和勞動報酬之外的利益,實際上就是將毒品進行了非法、有償轉讓,本質上屬于牟利行為,因此應當認定乙構成販賣毒品罪。這也符合毫不動搖地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的部署要求。
(作者:蔣濤 作者單位: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